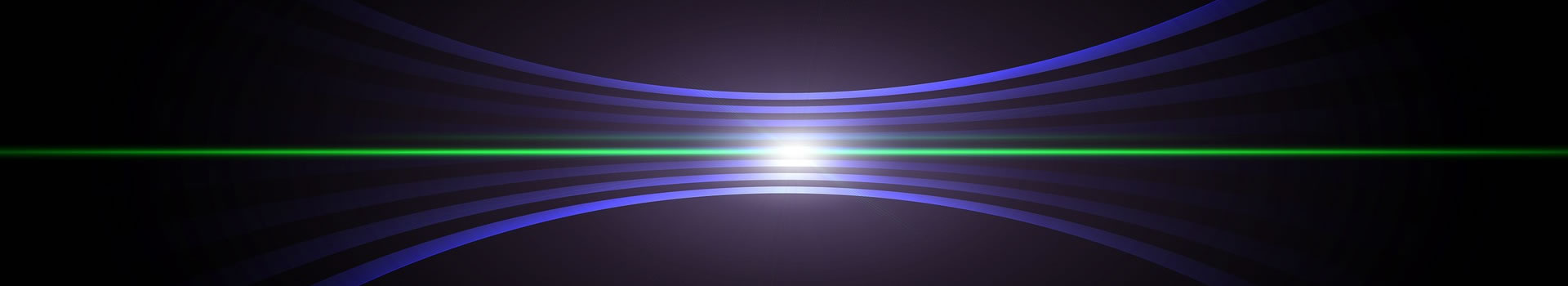
1953年1月,松花江面已冻作厚厚的冰层,哈尔滨站的站牌在呼啸寒风里晃动。一列军列缓缓进站,车门打开,一群披着旧棉大衣的年轻战士跳下月台,其中就有22岁的谭国玉。谁也想不到,短短数月后,这位一路从东北打到华南的四野老兵,会在课堂上被数学公式折磨得满脸通红。
那年春节还没到,部队提前动员了一批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去接受“现代科学火种”。哈军工刚刚挂牌,临时校舍是前中东铁路的红砖楼,窗户缝里灌着冷风,黑板却写满了导数与化学键。教室里坐的,有正儿八经的高中生,也有像谭国玉这样的连初中课本都没摸全的人。对后者而言,希腊字母比冲锋号更陌生。

谭国玉本来没想着读“洋书”。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时,他亲眼看着缴获的汽车因无人会修只好炸毁,心疼得直跺脚。战事一结束,他主动报名参加扫盲,可扫盲班刚结业,上级又说要送他进“速成中学”。结果汽车停在哈尔滨时,他才发现那所谓的“速成中学”,其实是全国最拔尖的军事工程学院。弄错地点已成定局,想退也退不回去了。
两周后,高中物理预备课一开讲,他彻底慌了神。摩擦系数、分子式、拉格朗日都听不懂,作业空白成了常态。摸底测试更惨:五门功课,四门亮红灯,一门勉强挂在及格线上。系里点名批评,说他“文化水平过低,影响教学进度”。谭国玉扛过爆破,扛过穿插,却扛不动黑板上的一连串未知数。他给原部队写信,恳求回去当连指导员,“打仗总比坐教室里好受”。
正在他收拾铺盖时,院长室来人:“陈赓院长让你过去。”这位新中国的上将正为学员的入学状况发愁。见面没寒暄,陈赓直接开口:“小谭,你想溜?”谭国玉低头:“报告院长,我底子太薄,学不起。”陈赓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打仗你说人在阵地在,读书却拔腿跑?不行,你死也得死在哈尔滨!”

这句直白而粗犷的话生生把谭国玉按在了学校。接下来的夜晚,教学楼、地下室、锅炉房轮流亮起小手电的光束,那是他翻教材时的影子。班干部查铺常常发现床板空着,久而久之传出“谭国玉又失踪”的笑谈。医生几次开了“强制休息”条,他却放下病号服又钻进教室。有人计算过,他平均每天睡不到两小时。
付出并不马上见效。第一次月考,他仍旧挂了两门。按照苏联顾问订下的硬杠子,只要一门不及格就得卷铺盖。副院长刘居英咬牙抗住压力,把谭国玉留成“预读生”,期限一年。消息一出,异样目光落在他身上,课堂后排嘀咕声此起彼伏。苏联专家克拉西霍夫更是直言:“这个兵不配穿学士服。”
逆风更激起当兵人的血性。谭国玉开始“抄作业”——不是抄答案,而是抄同学的学习方法。谁笔记条理清晰,他坐后排偷看;谁公式推导流畅,他课后追着请教。渐渐地,概念有了轮廓,习题也能写出第一行步骤。再次测验,他把原先的3分拉到50分。虽然只差一线,但班里已经有人意识到:这位“落后典型”真在往前冲。

转折点落在第二学期的大物理考试。监考席上坐着的正是克拉西霍夫,他特地多抽了两张题卡,摆明了要看笑话。答题结束后,他皱眉核分,5分满分,谭国玉连拿三个5分。教室瞬间鸦雀无声,苏联专家盯着答卷良久,才闷声说了句:“再考一次。”结果依旧。那天的消息传遍校园,学生食堂炸成一锅粥,连食堂大妈都指着谭国玉感慨:“这小子真能拚。”
陈赓听闻后,先是大笑,随即把人唤到办公室:“现在可不能歇气,越难的关越得顶上。”话虽如此,他还是递过一个暖瓶,“夜里别再跑去锅炉房,身子要紧。”
1954年夏,结业考核出分,谭国玉所有课程全部过线,几科还拿了优秀。他的学号前第一次出现红色五角星。两年前那个对牛顿定律呆若木鸡的老兵,如今能流利推导平动刚体方程。刘居英拍着表格,对周围人半调侃地说:“这就是解放军的算法——掉队的能冲到前头!”曾经质疑他的克拉西霍夫也改变了口风,替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为后来赴苏深造铺了路。

留苏归来后,谭国玉担任总参工程兵副部长,主持过多项国防工程建设。1986年,他出任工程兵指挥学院院长,整顿教学与科研,尤其重视“战场需求与工程技术”的结合。有人问他最难忘的人和事,他想了想,“如果当年陈院长让步,我现在还在营房里,哪有机会来研究火箭洞库?”
不少学者总结谭国玉的成长轨迹,都绕不开那句硬邦邦的话——“死也得死在哈尔滨”。一句话,扛起了一个人,也托起了一个时代对于“知识强军”的决心。若非如此执拗,一名普通指导员也许仍在营盘数着连队枪支;正因为这份执拗,后来才有工程兵跨江筑桥、飞速抢险的身影,也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技版图里一枚闪亮的名字——谭国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