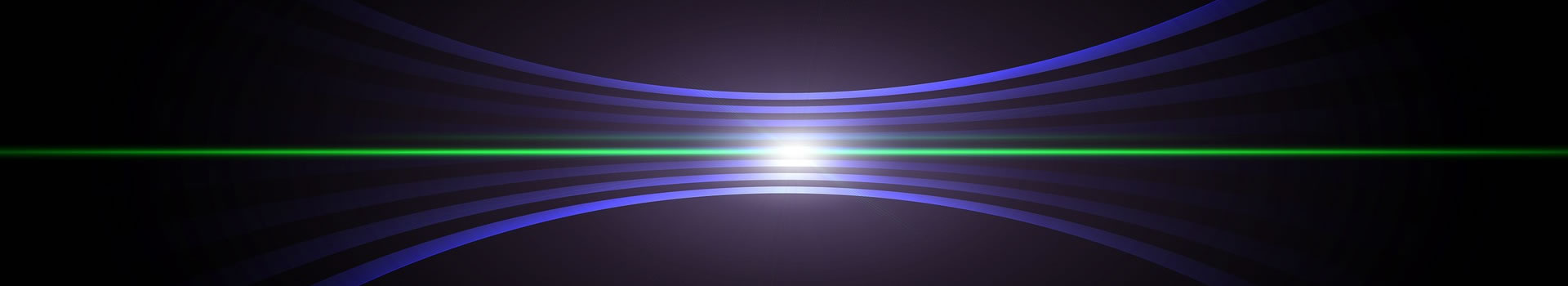
新时代、新规范(1927~1933)
无论他们争吵什么,受委任统治国都能在一个事情上达成一致:委任统治委员会内一定不能有德国人。法国在这一点上感受非常强烈,法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在1924年9月对比利时外交部部长保罗·海曼斯说,德国人怎样才能做到承担这种角色所需的“完全公正”呢?[1]比利时政府同意这种看法,但认为最好不要在国联行政院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基于原则的讨论可能会有利于德国。[2]目前,他们将会按兵不动。
他们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德国正在寻求加入国联。在观察了法国占领鲁尔引发的经济混乱及随后的通货膨胀之后,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得出结论认为,德国只有摆脱其贱民身份,才能重建其经济并恢复其国际地位。但是,他知道,加入“胜利者俱乐部”在对德国边界的缩小和帝国的消失感到愤怒的右翼政党中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德国在1924年9月29日的照会阐明了其申请加入国联的条件和保留内容,明确表示期望在管理委任统治地区的工作中发挥一定作用。[3]在1925年秋季洛迦诺(Locarno)谈判期间,施特雷泽曼重申了德国的主张。
施特雷泽曼的殖民修正主义多么严重?有些证据表明,他正试图两面讨好。当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和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告知他受委任统治国都无意放弃它们的委任统治地,德国能做的最好是在出现这种可能时提供其服务(大致和英国人对意大利说的一样),施特雷泽曼似乎非常镇静。他打消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德国殖民宣传的担心,解释说让极端主义者“释放精力”是明智的。[4]毫无疑问,他有足够的勇气进行斗争,因为由激昂的海因里希·施内(Heinrich Schnee)和平和的特奥多尔·塞茨(Theodor Seitz)(分别是前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洲总督)领导的三万多人组成的德国殖民协会(German Colonial Association)认为,德国应该利用加入国联之机坚持要求重新分割蛋糕。通过一连串的小册子、报纸文章、公开会议、议会(Reichstag)辩论,甚至向国联提出申诉,他们及他们的支持者们都反对德国被驱逐出帝国俱乐部,对承认德国殖民暴行(或者他们所称的“殖民谎言”)的要求进行抗议,把对处于受委任统治国管理之下的德国前领地遭忽视描绘得极其严重,并敦促把某些领土转移作为德国加入国联的条件。[5]
外交部非常明智,对这种杂音的大部分都不予理睬。“德国为了加入国联承诺遵守委任统治制度,这一吁求没有被认真对待”,外交部国际联盟处处长伯恩哈德·威廉·冯·布劳(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写道。他还乖戾地补充说,是政府,而不是殖民协会决定德国的对外政策。[6]然而,如果受委任统治国之前能够听取威廉大街[7](Wilhelmstrasse)发生的争论,他们就不会感到安心。殖民游说团体希望要回他们的领土,但外交部的目标稍微有些不同:重建德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的大国地位。在过去,殖民地对于建立大国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但如果归还殖民地是不可能的,他们将会寻找另一条道路。1924~1926年,有时经由与前殖民总督磋商,但有时也不与他们磋商,官员们就敲定了他们的战略。
首先,这一战略是以前多哥总督和1924~1935年任外交部殖民司司长埃德蒙·冯·布吕克纳(Edmund von Brückner)对德国殖民机会的聪明和极其务实的评估为基础的。布吕克纳认为,德国任何领地都不可能被归还。太平洋地区的委任统治地肯定是永久消失了,因为日本人把大量定居者送到他们被委任统治的岛屿,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把他们的领地视为抵制日本对北方威胁的缓冲区。非洲的前景也不是很光明,就像英国一直渴望坦噶尼喀,为了实现开普敦到开罗的控制,南非也一直希望把德国和英国的保护领地并入其北部地区。确实,英国可能愿意德国人回到西非(至少作为一种对抗法国的缓冲),但其所属喀麦隆和多哥的部分太小,在没有更大的法属部分的情况下,没有太大用处,而法国人(更不用提比利时人了)从未打算归还任何东西。
但即便如此,布吕克纳也不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在德国加入国联之前,他已经对英属喀麦隆的几乎所有德国人的种植园发起重购,到1925年时建立一个开发公司,在坦噶尼喀承担类似的收购。[8]而且,一旦加入国联并根据“门户开放”原则被赋予在委任统治地经商的权利,德国或许能“以经济方式渗透到我们的未归还的前保护领地……以至于将来这些领地归还德国不会成为不可能的事”。[9]在西南非洲,德国也可以通过进一步移民和经济援助支持现有的处于少数的德国人,以使这一领地,即使是处于南非的保护之下,变成“实质上德国的土地”。[10]
殖民协会主席特奥多尔·塞茨然后进行了评估,而且令外交部吃惊的是,他也比预料的更加务实。确实,他非常重视宣传,这给外交部造成很大麻烦,而且对于成为国联成员国的好处的看法也不如布吕克纳乐观,他指出英国毕竟允许德国在他们的领地上进行贸易,而法国肯定会——无论“门户开放”的义务是什么——找到某种方式把德国排除在外。但是,特别是从对法国在多哥统治的直言不讳的不满中,塞茨也发现了乐观的理由。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德国应该支持非洲人争取自治的那些愿望——因为多哥人肯定能够像利比亚人那样自己管理自己,而且,如果一旦给予自治,他们将会转向德国,寻求经济和政治指导。在西南非洲,德国也能派出移民,加强白人统治,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寻求推动这一地区走向更大程度的独立。通过支持民族自决的原则,换句话说,而不是仅仅要求得到一份殖民蛋糕,德国可以重新在其失去的殖民地获得影响力。[11]
外交部传阅了布吕克纳的备忘录和塞茨的备忘录,背后留下一串评论。[12]塞茨的评估不全被认为是有事实依据的,但官员们很欣赏他关于领土转移之可能性的现实主义看法,以及他们二人坚持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大多数官员也一致认为,德国通往全球大国的道路要经过日内瓦。作为国联行政院唯一一个没有殖民帝国的大国,坚持严格履行平等的经济准入和限制帝国主权的公认的国联规则,这是符合德国利益的。如果领土控制的好处是有限的,德国的劣势将会降低。在遭到来自外部的令人沮丧的多年批评之后,德国必须成为委任统治制度最机警的守护者。
在德国成为国联成员国期间,其官员采取了一种四分部的帝国战略。第一,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捍卫德国的殖民主张和殖民记录,绝不可以公开承认永远离开其殖民地。第二,他们会支持德国参与国联在殖民地地区开展的科学、技术、公共健康以及文化活动,以重建德国在这些地区作为领导者的声誉。第三也是重要的,他们将会努力工作,利用国联的“门户开放”要求,并以与其贸易利益一致的方式,寻求恢复德国在东非和西非的强大地位并努力打开新几内亚市场。第四,也是同样重要的,他们会竭尽全力地反对受委任统治国家把委任统治地与它们的殖民帝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任何行动,坚持它们作为处于国联集体控制之下并计划最终实现独立的自治领土的地位。
然而,为实现这些目标,德国在国联内必须非常强硬——特别是在委任统治委员会内部。在目睹了委任统治委员会发挥的作用,特别是法国在关于叙利亚的特别会议期间所承受的煎熬之后,威廉大街已得出结论认为,委任统治委员会是整个制度的关键。国联行政院太繁忙,国联大会太大,都不可能太把委任统治制度放在心上,但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成员们——特别是“中立者”西奥多利、拉帕德和范里斯——已经表现出准备掀开每一个盖子和暴露每一个缺点的意愿。国联的监督,曾被德国斥为掩盖吞并的遮羞布的国联的监督正变得真实。含意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们希望在对受委任统治政府的监督方面赢得真正的影响力,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获得一个在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的席位。”[13]
1926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年度国联大会上,德国获准加入国联。德国立即要求得到一个在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的席位。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因为法国和比利时坚决反对,而且自治领——在该委员会也没有席位——预见到拒绝德国人的前景。但英国的看法已经在改变了。“与完全排除它的参与相比,如果在委任统治委员会有其代表”,德国“很可能不是那么危险”;总的来说,英国殖民地部持谨慎的支持态度。[14]奥斯丁·张伯伦是不赞同的,但他同意以最可能促进欧洲和解的方式决定这一问题。[15]
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和往常一样夹在中间,努力进行调解。他理解这一问题对于德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16]如果英国试图推迟增补一名德国籍成员的话,它将会犯下一个重大错误,德拉蒙德在日内瓦对威廉·奥姆斯比-戈尔(现任殖民地部副大臣)说。[17]然后,他回到伦敦,向张伯伦重复了这一警告。德拉蒙德争辩说,对施特雷泽曼来说,不但用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成员头衔反对他国内的极端主义者更容易,而且他还愿意在任命的人选问题上做出妥协;后来的德国政府可能不会那么容易通融。[18]张伯伦未被说服,但当英国驻柏林大使拜访德国外交部要求德国鉴于自治领的强烈情绪不要讨论这一问题时,他被毫不含糊地告知德国认为这样的要求非常不友好。[19]施特雷泽曼愿意(短暂)延后,但他并不打算放弃原来的主张。
在次年春天,随着来自殖民游说团体的压力的增强,德国驻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和东京的大使们得到指示,再度提出这个问题。[20]除了日本政府外,其他都坚决反对,[21]但现在施特雷泽曼在国联行政院发挥着重要作用,承诺在6月国联行政院会议(图III-1)上提出这一问题。[22]公开争执的预期、德拉蒙德持续不断的压力以及施特雷泽曼私下做出的德国籍成员不会像海因里希·施内(德国外交部也发现他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样成为一个直言不讳的修正主义者的承诺,慢慢改变了奥斯丁·张伯伦。[23]在德拉蒙德巧妙的安排下,这一问题被作为一个次要的预算问题提交到国联行政院,国联行政院只是要求批准这一任命,因为国联大会已经投票支持了这些经费。作为一种礼貌,征求了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意见,张伯伦也表达了希望,即“它将会欢迎这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增补”。阅读了这些乏味的备忘录的人都没有察觉到隐藏在里面的感情。[24]

图III-1 1927年3月,国联行政院第44次会议,施特雷泽曼主持。坐在桌子上首位置的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埃里克·德拉蒙德和奥斯丁·张伯伦。
但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都非常愤怒,特别是在施特雷泽曼从日内瓦回国后在德意志帝国议会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进宣称取得胜利时。[25]英国的态度是“无法理解的,无法解释的”,菲利普·贝特洛在法国外交部对比利时大使说。张伯伦之前曾反对任命一位德国人;现在,他在没有提前让任何人了解其意图的情况下改变了自己的立场。[26]德拉蒙德和西奥多利一直希望一位德国籍成员加入委任统治委员会,但同时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法国和比利时代表直截了当地拒绝合作。皮埃尔·奥尔茨在1927年夏季的委任统治委员会会议上坚持认为,他们是一个技术性机构,而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他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当他的同事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或者,更糟糕地表示德国籍成员可能会做出某种非常有价值的贡献时,奥尔茨非常坦率地说,德国的殖民经验,如果有什么的话,也是不合格的。“德国为获得在委任统治委员会的一个席位而表现出来的热情是由于对委任统治制度特别关心并希望为维持《凡尔赛和约》确立的殖民机制做出贡献吗?”这几乎不可能,因为它最初提名的成员——他心中想的是施内——恰好是“体现德国反对殖民机制的那些人,而委任统治委员会构成了殖民机制的主要轮子”。如果国联行政院想要破坏委任统治制度,这就是他们的事情。委任统治委员会应该拒绝做出评论,并从备忘录中删除“这种糟糕讨论的所有痕迹”。拉帕德、范里斯和帕拉西奥斯进行的数小时的劝说完全未能改变奥尔茨和梅兰的看法,委任统治委员会只能这样记录,大多数都认为“任命一位新成员不存在技术性抗辩理由”,少数人鉴于“这一问题之政治特征”不发表看法。[27]
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国联秘书处就把谁任命到这一职位上进行了棘手的协商。[28]根据施特雷泽曼的建议选择的是路德维希·卡斯特尔,49岁,律师,德国全国工业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ies)领薪水的常务董事(图III-2)。卡斯特尔拥有丰富的殖民经验足以胜任专家——他曾经任德属西南非洲行政当局的助理财务主管,就德国的财产和利益与占领当局进行谈判一直工作到1920年——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工业说客和财政专家。他在战争后领导着德国财政部赔款处并参与了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的谈判,与他一起工作的协约国官员发现他很务实、高效而且精明。[29]卡斯特尔于1930年离职,因为不能再保留他在德国全国工业联合会的工作两年了,另外一位非常像他的人——尤利乌斯·鲁佩尔(Julius Ruppel),战前曾在喀麦隆政府内服务但在1924年之后在赔款委员会工作了6年——无缝地取代了他。[30]令人欣慰的是,一位德国全国工业联合会的秘书负责两人与国联秘书处之间的联系。

图III-2 路德维希·卡斯特尔。
卡斯特尔的任命并不受殖民游说团体的欢迎。[31]他们之前希望用他们自己的前总督中的一位来平衡卢格德,而且特别希望看到施内正面迎击敌人。(施内也不知羞耻地游说争取这一职位。)[32]然而,德国外交部发现卡斯特尔非常优秀,而且事实确实如此。虽然极其繁忙,卡斯特尔还是一丝不苟地为每一次会议进行了准备,对任何批评德国殖民记录的意见都提出质疑(应该暗示坦噶尼喀总督避免在未来做出这种声明,英国殖民地部指出),[33]努力争取让德国医生进入卢旺达,让德国的考古学家进入伊拉克,审查贸易协定和特许权以确保它们不会把德国排除在外或者违犯“门户开放”原则,并在柏林定期会见外交部官员和前总督以协调对任何兼并主义行动的反应。卡斯特尔正确的方式、完全传统的“土著政策”的看法以及公平公正的态度都使他免受公开的攻击。与此同时,如同德国外交部所指出的,他的存在加强了委任统治委员会中“中立者”的力量,并帮助它朝更加重要和独立的方向前进。[34]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分歧开始看起来不像受委任统治国和非受委任统治国之间——甚或帝国控制原则和国际控制原则之间的分歧那样深刻。未来,不但南非和法国的代表,而且英国和比利时的代表都会被迫处于守势。
因而我们可以把1927~1933年视为委任统治制度最具创新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德国的加入、意大利的修正主义、紧张的大国外交,以及不断加深的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在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致力于调解和合法化英国和法国的地缘政治目标的制度上炸开一个口子。突然间规则改变了,因为现在委任统治制度需要赢得迄今为止没有分到一份蛋糕的帝国的支持。由于受到其德国籍、意大利籍以及“中立的”成员的压力,委任统治委员会将会超越卢格德主义的理想,尝试加强以下两个核心的原则,这套制度就是以它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受委任统治国在委任统治地并不拥有主权,以及贸易和劳动必须是“自由的”。特别是德国的同意将决定国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这些规则被接受。
这些努力成败参半。如第7章所示,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确实成功地阻止了比利时、南非和英国的兼并主义行动,迫使国联行政院支持各帝国在委任统治地不拥有主权的原则。或者准确地说,它们拥有的不是法律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的主权;我们称为经济主权的东西不受限制地迅速发展起来。确实,如同两次大战之间的卢旺达——第8章进行讨论——所显示的那样,严格的国际审查使得比利时人加强了经济控制,停止了作为“土著习俗”的强制性和压榨性的劳动实践。法律主权和经济控制的脱钩含蓄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可以为委任统治地——以及隐含地,为各殖民地——设想什么样的“独立”?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看到的,英国在1929年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通过寻求国联承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伊拉克,尽管伊拉克的油田和机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英国控制之下,英国试图争取国际上赞同这种形式的独立,即在正式的帝国消失之后仍然能够捍卫地缘政治利益。在这个变幻无常的时期,在来自修正主义国家的压力下,我们开始瞥见世界上规范国家主权的一些轮廓,即便是1945年后伴随着国家能力的减弱。
1927年10月24日,路德维希·卡斯特尔参加了委任统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开幕式。这个夏季的“糟糕的讨论”已体现在印制好的备忘录中,卡斯特尔很清楚地知道他的一些新同事,特别是奥尔茨和梅兰如何看待自己的存在。“你是1914年以来和我说过话的第一位德国人,”奥尔茨直截了当地对卡斯特尔说。“幸运的是,我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卡斯特尔回答道,“我建议你以后对谁说话都要小心点。”在这次会议剩下的时间里,奥尔茨刻意保持着热情友好。[35]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AA,AE/II(2978)948,Herbette to Hymans,29 Sept. 1924.
[2] AA,AE/II(2978)948,Hymans to Herbette,28 Oct.1924.这种交流另见MAE,SDN 545。
[3] 这一照会附在“Letter from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League”,12 Dec. 1924之后,见LNOJ,March 1925,323-6。
[4] PA,R29433,Memo(Secret),14 April 1926.
[5] 海因里希·施内是一个特别高产和苛刻的宣传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为德国的殖民记录进行辩护并指责新的协约国政府的疏忽。施内与一位英国妇女结了婚,用英语和法语出版了几本这样的著作;特别参见The German Colonies under the Mandates(Berlin:Brönner in Nowawes,1922)和German Colonization,Past and Future:The Truth about the German Colonies(London:G.Allen & Unwin,1926)。特别是《殖民杂志》(Koloniale Rundschau)对所有德国前殖民地和国联的监督机制都保持着监督。有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殖民运动的历史描述正在激增。特别是集中关注纳粹时期的早期描述,见Wolfe W. Schmokel,Dream of Empire:German Colonialism,1919-1945(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关于经济计划,见Dirk van Laak,Imperiale Infrastruktur:Deutsche Planungen für eine Erschließung Afrikas 1880 bis 1960(Paderborn:Ferdinand Schöningh,2004)。
[6] PA,R95613,Von Bülow,“Aufzeichnung”,6 Jan. 1926.
[7] 德国外交部所在地。——译者注
[8] GStA PK,VI.HA,Schnee Papers,Box 31,Brückner to Schnee,30 April 1925.
[9] “...dass wir auch die uns noch nicht wieder zurückgegebenen früheren deutschen Schutzgebiete(abgesehen von dem japanischen Mandatsgebiet)wirtschaftlich in nicht zu langer Zeit so durchdringen,dass seine spätere Mandatsübertragung auf Deutschland nicht ausgeschlossen ist”. PA,R29433,Von Brückner,“Richtlinien unserer Kolonialpolitik”(1924);see also van Laak,Imperiale Infrastruktur,204-5.
[10] “zu einem in wesentlichen deutschen Lande würde”,in PA,R29433.
[11] PA,R29433,Seitz to von Schubert,3 March 1925,enclosing “Aufzeichnung über meine persönliche Auffassung der kolonialpolitishen Fragen”.
[12] 见PA R29433 Von Schubert to Seitz,11 April 1925及1925年3月19日和23日相关的备忘录。
[13] PA,R96524,“Kontrolle des Völkerbundes über die Mandate”,12 Aug. 1926;另见R96528,“Aufzeichnung. Zu Punkt 21 der Tagesordung der 43 Ratssitzung des Völkerbundes”,III.a.1.8173/26(27 Nov. 1926).
[14] NA,CO 323/965/6,Note by T. K. Lloyd,22 Sept. 1926.外交部和殖民地办公室官员之间的会议,继续概述了对1926年帝国会议的政策,也是谨慎支持的。见NA,CO 323/956/33,“Ques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Work of the Permanent Mandates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Memorandum Prepared for the Imperial Conference”,Oct. 1926,9-12。
[15] NA,CO 323/956/33,Note by Austen Chamberlain,19 Oct. 1926.
[16] PA,R29434,Von Schubert to Consulate(Geneva),1 Nov. 1926,and Aschmann(Geneva)to Von Schubert,11 Nov. 1926.
[17] NA,CO 323/956/34,Minute by Ormsby-Gore,16 Nov. 1926.
[18] LNA,S1608,no.3,Drummond,“Record of Interview”,17 Nov. 1926,very confidential.
[19] PA,R29434,Note,2 Dec. 1926.
[20] PA,R29434,Stresemann to Embassies,26 April 1927.
[21] PA,R29434,Report,7 June 1927.
[22] AA,AE/II(2978)948,Foreign Ministry to Colonial Ministry and Prime Minister,19 May 1927.
[23] PA,R96528,Stresemann Abschrift,26 April 1927.
[24] Minutes of the 45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LNOJ,July 1927,791,and LNA,Box R8,1/60184/248,Drummond to Theodoli,18 June 1927.
[25] Reichstag Debates,326 sitting,23 June 1927,11005.
[26] AA,AE/II(2978)948,De Gaiffier to Foreign Ministry,27 July 1927.
[27] 11 PMCM,133-40,170-1,178-83,200;quoted 139-40,180,200.
[28] LNA,S1608,no. 4,Memo by Gilchrist.
[29] 有关卡斯特尔的信息,见LNA,S 1608,no. 4,jacket 1,note by Gilchrist,9 Aug. 1927,and AA,AE/II(2978),948,Everts to Vandervelde,1 Sept. 1927。
[30] 有关鲁佩尔的信息,见Ruppel,see LNA,R2327,6A/19238/1143。
[31] PA,R29434,Seitz to AA,9 December 1927.
[32] GStA PK,VI.HA,Schnee Papers,Box 31,Schnee to Stresemann,9 Aug. 1927,and Stresemann to Schnee,30 Aug. 1927.
[33] NA,CO 691/100/27,Kastl to J. Scott,Chief Secretary to Government of Tanganyika Territory,10 Aug. 1928,and Note by Lloyd.
[34] 关于帕拉西奥斯的评论见PA,R96515,German Embassy(Madrid)to Foreign Ministry,12 March 1930,关于拉帕德的评论见PA,R96535,Dufour-Feronce to De Haas,1 July and 2 July 1929。
[35] NA,CO 323/986/1,G. Newlands to Ormsby-Gore,1 Dec. 1927,详细描述了在柏林与卡斯特尔的会谈。
#图文作者引入激励计划#

